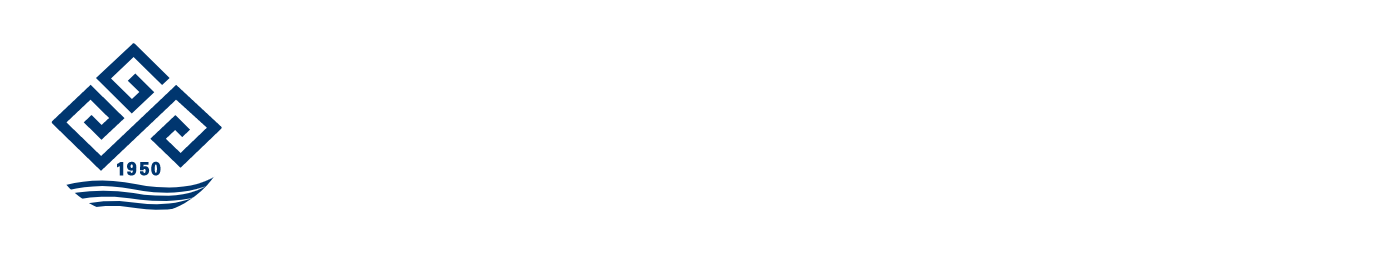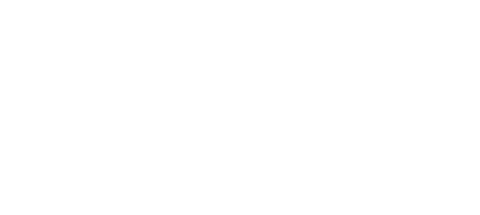《北京日報》10月11日第8版刊發文章《幸繪》,報道了我校藝傳學院何思倩老師用三年時間走遍京城,尋訪數十位京城“守藝人”,手繪了數百種瀕臨消亡的民間手工藝,并出版《幸繪京城守藝人》的故事,現將全文轉載入下:
門里門外,仿佛兩個世界。
門外,車流熙攘,眾生喧嘩;門里,老翁修筆,時光凝固。
這是廣義修筆店,年過八旬的張廣義戴著寸鏡,低著頭,守著斑駁的旋床、砂輪機、鋸床,專注地打磨著鋼筆尖……這活計,他已經干了幾十年。
一位姑娘走進店,她放輕腳步,左看看,右看看,然后駐足桌前,屏息凝神,生怕打擾到修筆的老人。老人并未抬頭,因為時常碰到這樣不修筆、只參觀的年輕人。
老人并不知道,這無聲的邂逅,被這姑娘視為一次幸會,催生出一場“幸繪”之旅。
姑娘叫何思倩,畢業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幸會張廣義時,她已經是北京工商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的教師。走出修筆店,老人修筆的耐心、從容總在何思倩的腦海里浮現。她索性拿起畫筆,涂抹之間,橘色燈光,修筆老人,漸漸浮現在白紙之上。
快速消費時代,傳統手工藝會不會逐漸消亡,該如何傳承與創新?這一直是何思倩心頭的困惑。端詳著畫中的修筆老人,她似乎找到了答案。“這樣的堅守,才是傳承的前提。”何思倩若有所思,她決定用畫筆記錄下這些堅守,讓更多的人了解、喜歡傳統手工藝,加入傳承的行列。
很快,何思倩和學生汪澤平、李嘉、黃孫杰、覃富理組成“幸繪手工藝偵探團”,開始鉆胡同,期待更多的幸會。
496米長的楊梅竹斜街,何思倩幸會做兔兒爺的張忠強。
中秋節,供兔兒爺!誕生于明末的兔兒爺,在北京家喻戶曉。楊梅竹斜街胡同口就有家兔兒爺鋪。店主叫張忠強,打小在琉璃廠一帶長大,爺爺和父親都是手藝人。幼時,家里并不富裕,能買個兔兒爺,是張忠強的夢想。上世紀90年代,張忠強師從老手藝人杜康民,開始學制兔兒爺。自此,他不僅圓了自己的夢,還用自己制作的兔兒爺,圓了不少孩子的夢。
張忠強為“幸繪手工藝偵探團”演示了打坯、合模、起模、蘸水、刷邊、修飾、壓光、扎耳朵、晾曬等制作兔兒爺的工序,他還和何思倩探討起提升兔兒爺“顏值”的創意。“看,這就是創新。”何思倩對學生們說。
每天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應該很幸福吧,其實張忠強也有憂心的事,“全北京會做兔兒爺的手藝人只有十多個了,因為這東西不賺錢!”張忠強的話讓何思倩更堅定了把“幸繪”做下去的決心,“殘酷現實下,還能堅守技藝,這更令人欽佩。”何思倩說。
第二次“幸繪”,是張忠強介紹的。
張忠強的鄰居是位木版年畫藝人,名叫張闊。他年少時是一名木匠,十年前一次旅行中初識木版年畫,便一見鐘情。從選取木料、繪制線稿、墨線印版、手工刻版、蘸取顏料、刷版上色、蓋上宣紙到套印,歷經八個步驟,運用十來種工具后,一張木版年畫才能出爐。這手藝費時費力,而且在數碼印刷流行的當下,并不叫座,張闊不僅沒賺到什么錢,還幾乎耗光了老本,但他還在堅持著,“任何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我不杞人憂天,只做好眼前事。”張闊平靜地說,他正忙著把書里記載的神像版畫全刻成拓版,“抓緊時間,為傳承這手藝做點事。”
在廊坊二條,何思倩“幸繪”了崔勇——正陽書局店主。這是一家專門收集舊書和老北京舊物件的書店。起初,何思倩并不明白,崔勇這個“80后”小伙兒,怎么會喜歡“故紙堆”,還為之辭了職,散了積蓄。“為了京味兒。”崔勇說得很認真,何思倩明白了,是對家鄉深深的愛,支撐著崔勇的堅守。
櫻桃胡同的扈氏毛筆,大柵欄西街的格格酥,鐵樹西街的內觀堂書店……年輕人們完成了一次次“幸繪”。當時,他們并未想到,這尋常巷陌之間的手藝竟掀起一場懷舊風潮。2015年9月,北京國際設計周,“幸繪手工藝偵探團”在大柵欄延壽街82號辦了一場“慢走大柵欄 速寫老手藝”的展覽,為“幸繪”做結。展覽專設“兔兒爺的秘密花園”創意涂鴉區,沒想到竟吸引了上千位觀眾參與。“一位住在附近的小姑娘,每天都要來畫幾張。”何思倩開心地回憶著。“幸繪”團隊趁熱打鐵,他們將記錄老藝人的手繪作品制成明信片,還與張闊合作,用木版年畫的手法呈現作品。
何思倩還想把“幸繪”集結成冊,她梳理出19次“幸繪”,呈現19位手藝人的堅守、巧工。隨后,她在網上發起眾籌,短短一個月,近500人認籌52803元,是目標金額的6倍多。9月,這本名為《幸繪京城守藝人》的書已順利出版。
“幸繪”仍在繼續——請手藝人辦講座,用新媒體推廣店鋪,尋訪更多的匠人故事……“‘幸繪’沒有終點。”何思倩說。
新聞鏈接:http://bjrb.bjd.com.cn/html/2016-10/11/content_727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