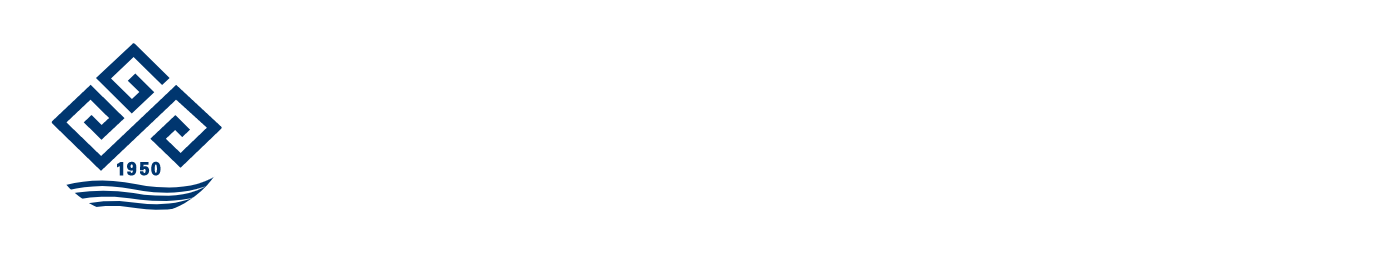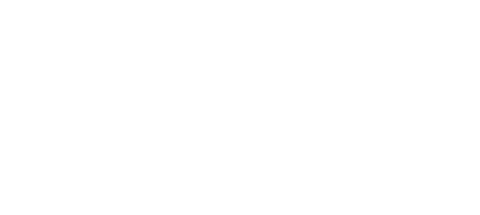與此同時,北京工商大學聯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北京農學院召開“大學生‘村官’選聘與后援工作研討會”,教育部思政司、市委教工委有關領導到會指導。來自京郊的大學生“村官”代表、基層村干部代表和高校領導及老師一起,討論如何做好選聘和后援工作,使大學生“村官”們“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動”。
北京市實施選聘大學畢業生擔任“村官”政策至今已3年,基本實現了“每村兩名大學生”的目標。這些“村官”65%為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其中碩士381名、博士1名。由于農村的環境與學校的環境有較大落差,加上大多數大學生村官是非農林院校、非農林專業畢業,明顯缺乏農村工作的知識與經驗,相當一部分大學生“村官”在工作、生活、心理上,都遇到不少困難,需要“扶上馬,送一程”。
據了解,北京工商大學自2006年底已有166名畢業生被選聘為“村官”助理,分布在房山、平谷、門頭溝等12個遠郊區縣,“村官”助理占畢業生的比例名列非農村院校前列。學校明確承諾:一是幫助村官助理解決工作中的疑難問題,二是對村官助理開放學校圖書館,三是歡迎村官助理回學校業余學習和開展文體活動,四是幫助大學生村官轉崗再就業。
北京房山區霞云嶺鄉四馬臺村村長助理廖朋業說:“剛到村里不久,有一個村民問我:‘你是大學生,那你告訴我,怎么能讓我掙更多的錢。’我當時語塞。這次聊天讓我認識到村民的熱情和直率,他們對我們的到來有著很深的期望。我們村風景很美,但在旅游資源管理和開發方面還有很多空間可挖掘。于是我就發揮自己旅游專業優勢,寫了一個規劃提綱給書記看,書記很支持。現在,我很希望能得到旅游、餐飲等行家的指點,真正為村子帶來財富。”
來自北京大興區民生村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大學生“村官”呂勤勤說:“村民們關心的問題都非常實際。即使自小生長在農村,我們回去也會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更別說我們中很多人沒有農村生活經驗。我們非常渴望能得到指點、幫助,遇到難題也會不由自主地跑回母校請教。比如平谷區馬坊鎮二條街村來自北京聯合大學的‘村官’王麗娜,因為村里草莓賣不掉,跑到母校求助,一時成了社會關注熱點,很多超市紛紛與她聯系,草莓一下子找到了銷路。”
房山區西路街道辦事處所轄的夏莊社區主任助理岳江魚說:“我是第一屆大學生‘村官’。負責村里水廠桶裝水的銷售。當時,我信心滿懷,因為這個工作跟我所學的企業經濟學專業非常對口。但沒想到不管怎么宣傳產品,客戶們的回應都很一般,后來我們發現良鄉地區桶裝水市場已經飽和。這讓我寢食難安。我試著給母校北京工商大學領導發了一條短信,說想為學校提供桶裝水服務。讓我欣喜萬分的是校領導非常支持,還到我們水廠作了實地考察。現在,學校師生喝的桶裝水就是我們提供的!學校還向我們這些已經畢業了的‘村官’贈送圖書館借閱卡,很多學生黨支部還與‘村官’所在的農村黨支部開展了‘紅色1+
房山區紙房村村委會主任李春生很直率地說:“農村需要能帶領農民致富、促進農村穩定的基層干部,大學生‘村官’們都是人尖尖,村民很稀罕。大多數‘村官’真做實事,比如給村里孩子辦輔導班、管理村里網絡、顯著提高了村里兩個市場的經營收入等。但也有一些大學生像水上的皮球,從上面看下水了,在下面看還漂在水上。”
會上,很多“村官”為北京市關于任職期滿大學生村官七項政策叫好,比如拿出一定數量的基層公務員崗位,面向合同期滿的大學生“村官”定向招錄;支持“村官”自主創業;舉辦面向“村官”的專場招聘洽談會等。“村官”廖貴云說:北京市委組織部、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剛剛發布公告,2009年首批3年期滿的大學生“村官”可于
研討會上,由北京高校心理素質教育工作研究基地聯合北京工商大學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等高校組成的大學生“村官”心理成長課題組還發布了部分研究成果。課題組認為:大學生“村官”無論在為新農村建設添磚加瓦方面,還是在轉變學生就業觀念、破解就業難題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調查發現,對競聘村官原因這個問題,大多數人的回答是到基層鍛煉成長走進農村了解民情和對“三農”問題抱有熱情。這說明“村官”們絕大多數具有理想信念和抱負,盡管農村經濟社會相對落后,位置偏遠,但他們仍然愿意投身于此。
調查發現,有79%的村官表示受到了當地各級領導的熱情歡迎,大學生村官的家長中有60%表示非常支持,35%表示比較支持子女去應聘村官,說明選聘大學生村官制度具有很好的群眾基礎。
調查發現,70%的村官表示在農村有所作為,95%的村官認為自己是合格的。但是村官們也表示,到任后需要3~6個月的適應期。另外,農村生活比較單調、同齡人很少,有些人在心理上有孤獨感,少數人明顯不適應,無明顯工作成績,有自卑感;個別人后悔當初的選擇。
總體上看,北京各高校普遍重視和關心村官選聘和后援工作。今后,高校應更加重視對村官的初選和村官成長過程中的心理支持,給予村官以思想上、能力上、心理素質等方面更多的關注和培訓,以幫助大學生“村官”更好更快地成長。
在房山區長陽鎮擔任“村官”的廖貴云同學感慨地說:“走出校門,才真正體會到學校的溫暖,既然選擇了做村官,遇到再大的困難我也不會退縮,因為我身后有一個堅強的后盾,那就是我的母校。”
《科學時報》